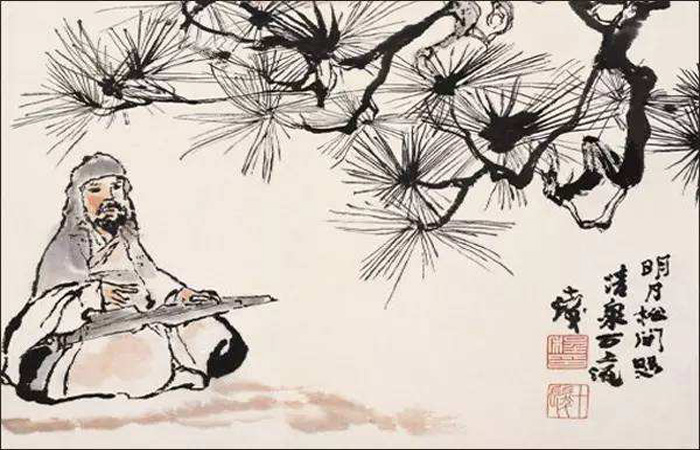現代社會非常發達,各個行業的就業機會都特別多,想要找到工作也相對比較容易。可是在古代社會,經濟發展完全不能和現代相比,除了務農之外,就業機會真的非常少。而對于向來自視清高的這些古代文人們來說,他們的求職之路往往會更加坎坷。
古代讀書人的活路很少,最通常的是:讀書為官。為了生計,或者按照社會的慣性,讀書人都免不了要為功名而奔走道途。而設若有更遠大的理想與抱負,要實現自己的文化價值,完成“修齊治平”的人生藍圖,則更需要積極主動地去獲取功名。

獲取功名,從隋唐開始就有了通途,這就是科舉考試。隋唐所確立的科舉制度,是中國社會制度的重大進步,從此來自社會底層的普通士子開始有了進人社會高層的途徑。
唐代從初唐到中唐都是充滿機會的時代,有不少士人或者不參加科舉,或者沒有中第卻得以人任。如陳子昂的友人,后來為陳編集的盧藏用,“初舉進土選,不調”,于是隱居終南山,學辟谷、練氣之術,但隱居之志并不堅定,《舊唐書》本傳云:“往來于少室、終南二山,時人稱為‘隨駕隱士’。”他的往來奔走果然奏效,并因此創造了一條號稱“終南捷徑”的求仕之路。此后,李泌、吳筠在考而不中時也走了這條捷徑。李白兩次進京,廣泛結交各界名流,又與吳筠等人一起隱居,從未赴舉,但卻令名聞于主上,終于在天寶元年,奉旨人京,與吳筠并待沿輸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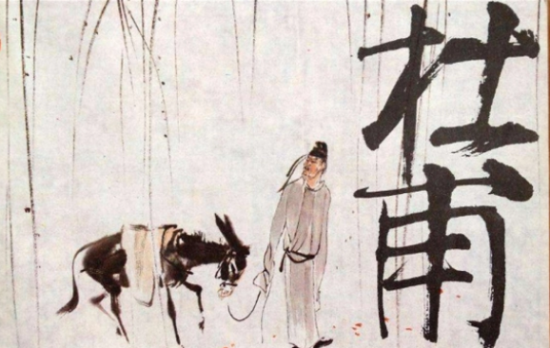
李白等人在求職上還算幸運的,比起上述諸人,杜甫更就要慘得多。二十四歲由州縣推薦參加進士試,杜甫滿懷希望而來,卻失敗而去,經過多年的學習與漫游,當他再次來到京城時,已經三十五歲,據《資治通鑒》記載,這年“上欲廣求天下之士,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。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奸惡,建言:‘舉人多卑賤愚聵,恐有俚言污濁圣聽。’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,灼然超絕者,具名送省,委尚書覆試,御史中丞監之,取名實相副者聞奏。既而至者皆試以詩、賦、論,遂無人及第者。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”。杜甫與元結都在這場政治騙局中上當了。
五年之后,在李林甫死后,杜甫在《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》中說到這次應舉失利的事,說:“破膽遭前政,陰謀獨秉鈞。微生沾忌刻,萬事益酸辛。”此后,他不得不像別人一樣到處投獻詩文,如汝陽王李班、尚書左丞韋濟、翰林學士張咱、京兆尹鮮于仲通等人的宅第他都去敲過門、投過文,但這些努力都沒起作用。奔走長安的這些年里,他生活的狼狽和心靈的苦痛,在《奉贈韋左丞二十二韻》一詩中有極真實、深刻地描繪,抄錄其中一段于下:
甫昔少年日,早充觀國賓。讀書破萬卷,下筆如有神。賦料揚雄敵,詩看子建親。李邕求識面,王翰愿卜鄰。自謂頗挺出,立登要路津。致君堯舜上,再使風俗淳。此意竟蕭條,行歌非隱淪。騎驢三十載,旅食京華春。朝扣富兒門,暮隨肥馬塵。殘杯與冷炙,到處潛悲辛。

顯然,奔走權門、干謁貴幸的屈辱,正在消磨他的壯志、摧殘他的生命。如果說二十四歲那次的失敗,他并不很在意,在“放蕩齊趙間,裘馬頗輕狂”的漫游中,他的壯心得到培養,那么此時備嘗生活困頓之苦、人情冷暖之態的詩人,再也輕狂不起來了,他像一只受傷的鳥垂著翅膀從青天落在塵土中。還好,當他向玄宗“延恩匭”投獻三大禮賦后,“文采動人主”,如“一日聲炫赫”,玄宗命宰相在集賢院考他的文章,于是,“集賢學士如堵墻,觀我落筆中書堂”(《莫相疑行》)。不過,他只獲得一個“參列選序”的資格,幾年之后,他才被授右衛率府兵曹參軍,一個管理東宮宿衛、儀仗的卑官。一個一再自比稷契的人,經過十年的掙之路的結局!最終為了生計接受了一個從九品的微官,這就是杜甫艱難求仕之路的結局。
古代文人們能夠順利入仕的不多,還有非常多的文人終其一生,也無法得到統治階層的青睞,只能通過詩文來宣泄心中的苦悶。這些詩文流傳至今,已經成為了中華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 手機版|
手機版|

 二維碼|
二維碼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