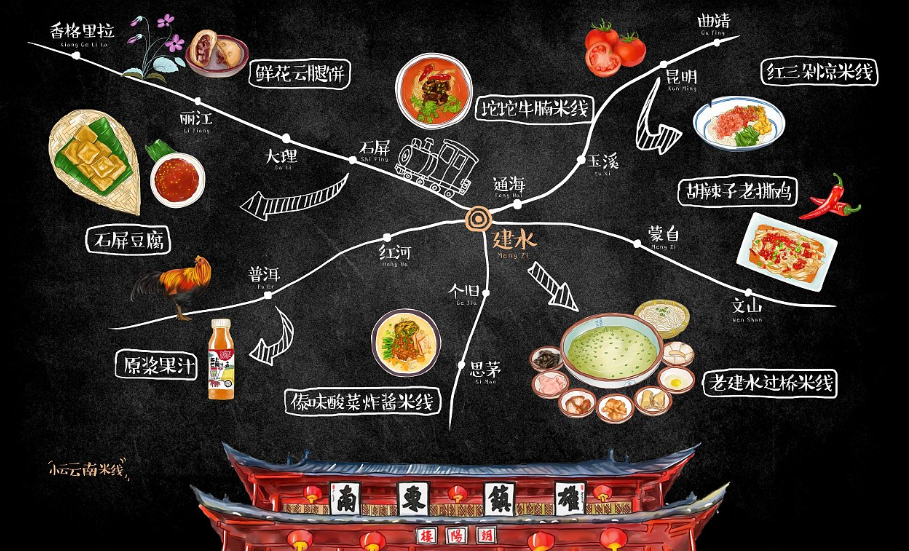說老廣在吃上有一套,沒人有意見吧。
無論是堂上酒席,還是街邊小攤,廣東人都能吃出“前菜主菜湯品甜點”的全套感來。
更有意思的是,那道你以為只是“錦上添花、如果沒有也無傷大雅”的小甜品,廣東人也絲毫不懈怠。甚至,用上了“燉熬煮”等諸般伺候老火靚湯的絕密大法,各家使各家的絕招,最后以廣府、潮汕兩大門派平分江湖。
只不過,這“甜品”二字聽起來總不夠老廣,地道的說法叫“糖水”,簡單而俗常,更符合廣東人的性格。要知道這廣東人的糖水,是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,自然不會像一碟“擺盤大過內涵”的高檔甜點。
它或許是家里阿婆熬給過幾代人吃的方子;也或許,是沿街幾十年的糖水鋪三塊五塊一碗賣給老街坊的食物;更可能是一個廣東人從童年、戀愛,到成家,再到有下一代的全程陪伴。

說“冇糖水,不廣東”,一點也不夸張。
如果你以字面意思去理解廣東的糖水,那可就太“單純”了。
廣東的糖水是甜品的總稱,有稀有稠、可飲可食,無論口感、滋味,其層次感、跨越度都超乎一般人的想象。據不完全統計,廣東糖水的品種多達300多道,更別說各地各家還有不同風味上的差別。
傳統的“二沙三糊”是基本:紅豆沙、綠豆沙,芝麻糊、杏仁糊、核桃糊。和所有菜系的基本款一樣,這幾道看似簡單的糖水單品,往往最能見真章。
地道的廣式紅豆沙里會下陳皮,綠豆沙則要與海帶和臭草相配,既為佐味,也是食性間的平衡哲學。對于吃慣了老味道的廣東人,一碗沒有臭草味的綠豆沙,就像沒有靈魂一樣。

春季燜雪梨,夏季煮馬蹄,秋季燉銀耳,冬季吃湯圓。
連糖水都要吃出四季時令的差別來,這種事,大概也只有對吃一點都含糊不得的廣東人才干得出來。
四季糖水,其食材的搭配源自廣東人講究藥食同源、不時不食的“執念”,“夏秋去暑燥,冬春防寒涼”。冬時用生姜、桂圓等散寒溫里,一到暑氣逼人的盛夏,就得拿出諸如馬蹄、竹蔗、茅根之類,一解暑熱之氣。
糖水王國的另外一層維度,與地域物產有關。
不同的物產,增加了廣東糖水的豐富度。比如自古以來就是制糖中心的潮汕地區,其糖水的風味更突顯“甜味”,因而也被稱為“潮汕甜湯”;再比如,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長久以來有養殖水牛的傳統,出產的濃郁醇厚的水牛奶,也讓這一帶出現諸如順德雙皮奶、沙灣姜撞奶、大良鳳凰奶糊等糖水界的絕佳奶制品。
另外,嶺南地區品種繁多、產量豐富的水果遇上廣東人的糖水,更是描繪了一張水果系糖水圖鑒,芒果、椰汁、荔枝、柚子、木瓜……統統可以拿來入藥,不對,入糖水!

小時候看TVB劇,看與廣東同根同源的香港,鏡頭里常會出現這樣一幕:警組老大拎著一袋糖水給加班的組員吃,一組人開開心心、齊齊整整,邊吃糖水邊聊案情。
糖水,對廣東人來說,似乎早就超過食物本身的意義,變成一種生活。
吃完飯,得出門和街坊吃個糖水聊聊天;談戀愛時先約個糖水鋪,在浪漫感與煙火氣之間,氛圍拿捏得剛剛好……或許,對于其他地方,甜品確是錦上添花的東西;但對于廣東人,糖水是“必需品”,它從未跳出生活本身。
廣東人啊,怕就是糖水做的。
汪曾祺寫過一篇《炸彈和冰糖蓮子》,后來情節被用在了電影《無問西東》里。
汪老回憶,在西南聯大時,有“跑警報”的說法。那時候,日本飛機三天兩頭轟炸,一有警報,同學們就都從校舍跑到野地里去。但有一位鄭姓的廣東同學,經常不跑警報,他干什么呢?他留下來煮冰糖蓮子。
“一有警報,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。警報解除了,他的蓮子也爛了。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,昆中北院、南院,都落了炸彈,這位老兄聽著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,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。”
廣東人有多愛糖水,直接上街也能看出幾分。
在廣州老城區越秀,有一條幾十年的糖水街——文明路,數十間糖水老鋪開在傳統騎樓老街,裝修或不起眼,卻永遠門庭若市。百花、玫瑰、明記,即便相距不遠,但因各家有各家的風味絕招,幾十年來各自相安無事、生意興隆。
還有更多藏在社區里的糖水鋪、穿梭在街巷間的糖水推車……正是這一碗碗帶著些許古早味的糖水,慰藉著一代代老廣們的身體與靈魂。
每一個離家的廣東仔,回到廣東,總要續上一碗當地的糖水。
那或是家人煲的,帶著“婆婆媽媽”的味道;或是來自那些吃慣了的街頭小鋪,是從兒時就習慣的配方。只要喝上一碗,身體就好像知道“回家了”。
前陣子廣東疫情期間,有個暖心的小故事讓人印象深刻:有市民點了30份冰鎮綠豆沙給檢測點的工作人員。

這是彌漫在廣東糖水里,深入人心的人情味。
聽過一個傳聞,講一間廣州的糖水鋪,開了幾十年只漲了一塊五毛錢。別人問老板,為什么不漲價?老板說,“不舍得啊,感覺對不起街坊”。
但事實上,跟著物價漲幅調節售賣價格,實在也已是良心買賣。
然而,對于一間幾十年開在一個地方的小店,或許,它的存在,已經不僅僅只是買賣。
一買一賣之間,一來一往之間,一碗糖水的背后,包含了幾十年的人情,是人與人從陌生到熟悉,從猶疑到信任的轉變。
當今社會,一家廣式甜品店并不難找。
在我們生活的城市,隨便逛一家商場,或者更簡單,動動手指打開一個外賣App,就能吃到幾家賣廣式甜品的。但即便味道也還不賴,與廣東當地的糖水鋪相比,卻還是會感覺少了一點什么。好像糖水離開廣東,就不可避免少了一點鮮活的、恒久的、靈魂的東西。
或是潮濕氤氳的南方氣候;或是熱絡擾攘的街巷煙火;更或是這種種背后,每一個好好生活、又重情重義的廣東人。
 手機版|
手機版|

 二維碼|
二維碼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