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國冶鑄生鐵技術(shù)的起源之早、發(fā)展之速,在世界冶金史上占據(jù)著獨(dú)特而重要的地位。追溯其根源,主要得益于青銅時代的技術(shù)積淀和鼓風(fēng)技術(shù)的應(yīng)用。
1、青銅時代的技術(shù)積淀
殷墟的鑄銅作坊分布廣泛,其中較為重要的有三處:小屯東北地鑄銅遺址、苗圃北地鑄銅遺址和孝民屯。這些作坊的遺跡現(xiàn)象復(fù)雜,功能分區(qū)明確,涵蓋了從原料加工到成品鑄造的完整流程。
小屯東北地鑄銅遺址位于殷墟宮殿宗廟區(qū)的東北方向。該遺址的遺跡現(xiàn)象較為復(fù)雜,兼之發(fā)掘年代久遠(yuǎn),學(xué)者們對其鑄銅遺址和基址的年代關(guān)系存在爭議。岳占偉等學(xué)者傾向于認(rèn)為該鑄銅作坊的主體(大連坑除外)始建年代和鼎盛時期可能早于殷墟時期,很可能屬于洹北商城時期。隨著宮廟基址的建設(shè)和擴(kuò)大,鑄銅作坊逐漸沒落和消亡。
苗圃北地鑄銅遺址位于殷墟的中部偏北區(qū)域。苗圃北地鑄銅遺址的考古發(fā)掘揭示了當(dāng)時青銅鑄造的多個環(huán)節(jié),包括陶模、陶范的制作、熔爐的設(shè)置以及鑄造后的加工處理等。
孝民屯鑄銅遺址是殷墟最大的鑄銅遺址之一,經(jīng)過多次發(fā)掘,遺址可分為東、西兩區(qū)。西區(qū)的鑄銅遺址位于孝民屯村西和村址南部,東區(qū)的鑄銅遺址位于村東南。遺址內(nèi)發(fā)現(xiàn)的鑄銅遺存以殷墟三期和四期為主,二期較少,一期闕如。孝民屯鑄銅遺址的使用時間較長,出現(xiàn)于殷墟二期,發(fā)展和繁榮于殷墟三、四期,消亡于商周更替之際。
東、西區(qū)的鑄銅作坊在功能上有所分工,西區(qū)的制作工序較為完整,而東區(qū)可能存在制范(以制陶為主)和鑄造工序(以金屬工藝為主)的分離。在殷末期,鑄造重心由西區(qū)轉(zhuǎn)移到東區(qū)。此外,孝民屯鑄銅遺址出土了大量陶范,數(shù)量達(dá)7萬余塊,這些陶范的種類豐富,涵蓋了當(dāng)時常見的青銅器類型。
這些鑄銅作坊出土了大量與鑄造相關(guān)的工具和設(shè)備,出土的熔銅工具包括熔爐及配套的鼓風(fēng)嘴等。這些熔爐殘片表明,當(dāng)時的熔爐設(shè)計合理,能夠承受高溫并多次使用。例如,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鑄銅遺址出土的熔爐殘片表面粘有銅液,且多數(shù)有數(shù)層襯面,每層襯面均粘有銅液,證明其多次修繕和使用。鑄銅工具則包括各種模范,以禮器范最多。此外,還有用于制范及修飾銅器的銅刀、銅錐、骨錐等器物,當(dāng)時的工匠不僅掌握了復(fù)雜的鑄造技術(shù),還能夠?qū)η嚆~器進(jìn)行精細(xì)的修飾。
考古學(xué)家陳夢家通過對安陽出土的泥模和陶范的研究,明確指出殷墟時期的青銅器是通過陶范直接鑄造的。這種鑄造方法需要工匠們制作出精美的泥模,并在泥模上刻鏤花紋,再用泥模制作陶范。陶范的接合通常采用榫卯結(jié)構(gòu)(“子母口”),以確保鑄造過程中各部分的緊密結(jié)合。
殷墟青銅器的鑄造工藝復(fù)雜且精細(xì),主要采用陶范鑄造法。出土的陶范根據(jù)外觀可分為兩類:I式范背后有一凸棱作為凸榫,需鑲嵌在背范上拼合使用;Ⅱ式范背后存在多個指窩,便于把持和脫模,邊緣有榫卯用于扣合。此外,殷墟出土的青銅器中,許多器物的表面裝飾有精美的紋飾,這些紋飾的制作需要復(fù)雜的工藝和高超的技藝。孝民屯鑄銅遺址出土的陶范中,有部分殘片的原料在原生土內(nèi)加入了砂粒和蚌粉,甚至加入了植物莖葉,以提高其耐高溫性能。
以“婦好銅鸮尊”為例,其鑄造工藝極為復(fù)雜。該青銅器高46.3厘米,口徑16.4厘米,重16.7千克。鸮尊的造型為一只站立的貓頭鷹,其頭部和身體部分分別鑄造,再通過鑄接工藝連接在一起。鸮尊的表面裝飾有精美的紋飾,包括羽紋、云紋和雷紋等,這些紋飾不僅增加了器物的美觀性,還具有宗教和象征意義。

(婦好銅鸮尊)
殷商時期的青銅器主要以錫青銅和三元青銅(銅、錫、鉛)為主,鉛青銅較少。在殷墟出土的青銅器中,錫含量較高,當(dāng)時的工匠已經(jīng)掌握了通過增加錫的比例來提高青銅硬度的技術(shù)。此外,殷墟青銅器的成分分析顯示,其合金配比已經(jīng)相當(dāng)成熟,能夠根據(jù)不同用途調(diào)整成分。
青銅禮器通常使用高錫青銅,錫含量較高,以增強(qiáng)硬度和光澤。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青銅器中,錫含量普遍較高。
青銅兵器如青銅戈的成分分析顯示,其銅含量在80%左右,錫含量在10%-20%之間,鉛含量較低。這種配比使得兵器具有較高的硬度和韌性,適合實戰(zhàn)使用。
青銅工具如斧斤等工具,銅與錫的比例通常為5:1,即銅占83.33%,錫占16.67%。這種配比的青銅工具具有較高的強(qiáng)度和耐磨性,適合砍伐等重體力勞動。
通過對殷墟出土的約200件銅器的化學(xué)成分分析,發(fā)現(xiàn)當(dāng)時的工匠對青銅合金配比與機(jī)械性能的關(guān)系已經(jīng)有了相當(dāng)深入的認(rèn)識,并且對操作有嚴(yán)格的控制。這種科學(xué)的配比技術(shù)使得青銅器的性能能夠滿足不同的使用需求。
盡管《考工記》中記載的“六齊”(青銅合金的六種配比)是戰(zhàn)國時期的文獻(xiàn),但其內(nèi)容反映了中國古代青銅鑄造技術(shù)的標(biāo)準(zhǔn)化趨勢。例如,制造鐘鼎的銅與錫的比例為6:1(銅占85.71%,錫占14.29%),這種配比的青銅器質(zhì)堅且有韌性,聲音洪亮。類似的標(biāo)準(zhǔn)化配比在殷商時期已經(jīng)有所體現(xiàn),說明當(dāng)時的工匠已經(jīng)能夠根據(jù)不同的用途選擇合適的合金成分。
“后母戊大方鼎”是世界上已發(fā)掘的最大的一件青銅器,重達(dá)875公斤。從鑄造后母戊大鼎這樣的大型青銅器來看,整個生產(chǎn)過程需要130多人同時施工。包括運(yùn)土、備料、制模、制范、制芯、合范、焙燒、合金熔煉、鼓風(fēng)、澆注、清理、打磨等多個環(huán)節(jié)。這種復(fù)雜的生產(chǎn)流程,必須依托于嚴(yán)格的組織管理,才能完成各個部門之間的協(xié)調(diào)。

(后母戊大方鼎)
2、鼓風(fēng)技術(shù)的早期應(yīng)用
我國煉鐵技術(shù)在煉銅技術(shù)的基礎(chǔ)上逐步發(fā)展起來的。銅綠山古礦冶遺址位于湖北省大冶市城區(qū)西南約3公里,是一處西周至漢代時期的銅礦開采與冶煉遺址,總面積約8平方公里。遺址南北長約2公里,東西寬約1公里,遺留的煉銅爐渣40萬噸以上,占地14萬平方米左右。
銅綠山古礦冶遺址的礦井由豎井和巷井(平巷)組成,古代工匠用木材制成的方形框架作為井巷的支護(hù),已能承受巷外的壓力,保證豎井和平巷的暢通,使礦工能在距地表40-50米的深處采掘。并巷框架大多用榫卯法,即在四根方木或原木的兩端砍鑿出長榫或榫孔,相互穿接而成。框架之間用木棍、木板或竹索相接,形成一個整體。
排水是通過木質(zhì)水槽把地下水引導(dǎo)儲水井,或利用專門的排水巷道,用木桶將水經(jīng)豎井提出地面。通風(fēng)是利用坑口的高低不同產(chǎn)生的氣壓差而形成的自然風(fēng)。

遺址內(nèi)已清理出各種采礦井巷數(shù)百條,生產(chǎn)、生活用具上千件,還有多種形式的煉銅爐,并發(fā)現(xiàn)有春秋時期的煉銅爐8座。已發(fā)現(xiàn)的采掘工具包括木鏟、木耙、木槌、銅斧、銅鑄、鐵鋤、鐵鏨、船形木斗和轆轤等。
銅綠山已經(jīng)采用了鼓風(fēng)豎爐煉銅,冶銅溫度為1200℃左右,并已具備連續(xù)加料、連續(xù)冶煉,間接排放渣液和銅液的功能。冶銅技術(shù)在“氧化礦—銅”工藝基礎(chǔ)上,發(fā)明了“硫化礦—冰銅—銅”工藝。通過科學(xué)檢測,東周時期爐渣平均含銅量0.7%,接近于現(xiàn)代冶銅排渣標(biāo)準(zhǔn),粗銅純度高達(dá)93%以上,這在當(dāng)時世界上處于遙遙領(lǐng)先的地位。
大冶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出土的三座保存完整的煉銅豎爐,展現(xiàn)出當(dāng)時煉銅設(shè)備的先進(jìn)性。這些豎爐呈圓錐形,由爐基、爐缸、爐身三部分構(gòu)成,爐基筑于地下,設(shè)有通風(fēng)溝,爐缸架于其上,內(nèi)外壁用不同材料夯筑,爐身高度經(jīng)推算可達(dá)1.2-1.5米。爐旁還筑有工作臺,用于加料與放置鼓風(fēng)設(shè)備。同時,熔銅設(shè)備既有中型、小型坩堝爐,也有大型熔銅爐。

(煉銅豎爐)
我國古代的煉鐵爐,在煉銅豎爐與熔銅堝爐的基礎(chǔ)上發(fā)展出高爐(豎爐)與坩堝爐兩種主要形式,用于冶煉鑄鐵。
高爐的前身是豎爐,這種爐型在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。1987年10月29日至11月7日,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西平縣文化局聯(lián)合對西平縣出山鎮(zhèn)酒店村的治煉爐進(jìn)行了搶救性發(fā)掘。此次發(fā)掘清理出了一座保存較為完整的戰(zhàn)國時期冶鐵豎爐。該豎爐呈橢圓形,爐體高大,爐缸較窄,采用水平鼓風(fēng)。這種設(shè)計有利于提高爐內(nèi)溫度和燃中燒效率,適合大規(guī)模生產(chǎn)生鐵。
爐子的上部和下部呈喇叭形,中間為細(xì)腰,整體結(jié)構(gòu)堅固耐用。該豎爐使用鼓風(fēng)設(shè)備,通過強(qiáng)力鼓風(fēng)使?fàn)t內(nèi)溫度達(dá)到1400℃以上,能夠?qū)㈣F礦石還原并滲碳童形成液態(tài)生鐵。爐內(nèi)使用石灰石、螢石等作為助熔劑,與礦石中的二氧化硅生成液態(tài)爐渣,渣和鐵在爐缸中自然分層,再從鐵口放出。
成熟的高爐在東漢時期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,其結(jié)構(gòu)包括爐體、鼓風(fēng)設(shè)備和出鐵口等部分。高爐通過分層加入碎鐵礦石與木炭,并鼓風(fēng)燃燒,使鐵礦石在高溫下還原為液態(tài)生鐵。高爐的出現(xiàn)極大地提高了煉鐵效率。其連續(xù)供料和連續(xù)出鐵的方式,使得煉鐵過程更加自動化和高效。
坩堝爐是另一種重要的煉鐵爐型,其發(fā)展同樣基于早期的熔銅技術(shù)。坩堝最早用于熔銅,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商代。商代的坩堝主要由耐高溫粘土制成,用于熔化銅礦石。坩堝爐采用“內(nèi)加熱”法,將銅料與木炭一同加入爐中并鼓風(fēng)燃燒,熱效率較高。
在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,坩堝爐開始用于煉鐵。其原理與熔銅類似,通過分層加入碎鐵礦石章與木炭,并鼓風(fēng)燃燒,使鐵礦石在高溫下還原為液態(tài)生鐵。坩堝爐的靈活性較高,適合小規(guī)模生產(chǎn),能夠根據(jù)需要調(diào)整爐溫和爐內(nèi)氣氛。
湖南長沙楊家山65號墓出土的鐵鼎表明,當(dāng)時的工匠已經(jīng)能夠使用坩堝爐鑄造復(fù)雜的鐵器。1976年,湖南省長沙市楊家山65號墓出土了一件春秋晚期的鐵鼎。這件鐵鼎是中國迄今發(fā)現(xiàn)的最早的鑄鐵容器之一,鐵鼎為敞口、豎耳、圓腹、平底,有短小的蹄足。殘高6.9厘米,足長1.2厘米。經(jīng)金相學(xué)鑒定,該鐵鼎為白口鑄鐵件。

(湖南長沙楊家山65號墓出土的鐵鼎)
無論是高爐還是坩堝爐,鼓風(fēng)技術(shù)都是提高爐溫、促進(jìn)燃料燃燒的關(guān)鍵。
皮囊鼓風(fēng)技術(shù)是中國古代冶金技術(shù)的重要組成部分,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時期。這種鼓風(fēng)設(shè)備通常由整張皮革制成,兩端收緊,中間鼓起,通過人力操作,將空氣壓入冶煉爐中,從而提高爐溫。這種技術(shù)的應(yīng)用,使得青銅器的鑄造成為可能,因為青銅的熔點(diǎn)約為1000攝氏度,沒有鼓風(fēng)設(shè)備,很難達(dá)到如此高的溫度。
洹北商城的鑄銅遺址是近年來殷墟考古的重要發(fā)現(xiàn)之一。考古學(xué)家在該遺址發(fā)現(xiàn)了6件陶質(zhì)鼓風(fēng)嘴,這些鼓風(fēng)嘴長約5厘米,一端與皮囊連接,用于往窯爐里鼓風(fēng)輸氧,以使燃料加速燃燒增加爐溫。這些鼓風(fēng)嘴表面粘有銅渣,它們曾用于鼓風(fēng)以輔助銅器鑄造。此外,該遺址還發(fā)現(xiàn)了熔銅坩堝殘片、銅器碎片及打磨銅器的圓形礪石等重要遺物。

(洹北商城鑄銅遺址陶質(zhì)鼓風(fēng)嘴)
隨著冶鐵技術(shù)的發(fā)展,特別是鑄鐵技術(shù)的發(fā)明,對爐溫的要求顯著提高。鑄鐵的生產(chǎn)需要更高的溫度,以使鐵礦石充分熔化并形成液態(tài)鐵。傳統(tǒng)的鼓風(fēng)設(shè)備主要由皮囊(橐)和鼓風(fēng)管(籥)組成,這種設(shè)備雖然能夠提供一定的風(fēng)量,但存在明顯的局限性。
首先,皮囊鼓風(fēng)的風(fēng)量有限,且風(fēng)壓較低,難以滿足大型煉爐的需求。其次,傳統(tǒng)鼓風(fēng)設(shè)備的效率較低,需要大量人力操作,如《吳越春秋》記載,吳王闔間鑄造“干將”“莫邪”兩把寶劍時,曾使用“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”,當(dāng)時煉爐上使用的橐數(shù)量眾多,且需要大量人力操作。
為了滿足更高的爐溫需求,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鼓風(fēng)技術(shù)進(jìn)行了多項改進(jìn)。《老子·道經(jīng)》記載:天地之間,其猶橐(tuó)龠(yuè)乎,虛而不屈,動而愈出。這是目前所見關(guān)于“橐龠”的最早記載。橐是用牛皮制成的大袋,兩端收緊,中間鼓起。
《墨子·備穴》記載:具爐橐,橐以牛皮。爐有兩瓿,以橋鼓之。百十每,其重四十斤,然炭杜之。滿爐而蓋之,毋令氣出。當(dāng)時的鼓風(fēng)設(shè)備采用了兩個皮囊交替鼓風(fēng),通過牛皮制成的風(fēng)箱(橐龠)和杠桿(橋)的作用,提高了鼓風(fēng)的連續(xù)性和效率。此外,《管子·揆度》中提到:搖爐橐,而立黃金也。當(dāng)時的冶煉金屬已經(jīng)普遍使用皮橐鼓風(fēng),通過風(fēng)通過皮橐小孔上安裝的“籥管”壓入冶鐵爐,使燃料燒得更旺,從而提高爐溫。
3、漢代冶鑄生鐵技術(shù)的普及
從現(xiàn)有資料來看,戰(zhàn)國時期冶鐵遺址的大規(guī)模系統(tǒng)發(fā)掘尚不充分,但大量出土的生鐵鑄件足以證明,當(dāng)時生鐵已成為冶鐵業(yè)的主流產(chǎn)品。據(jù)文獻(xiàn)記載,戰(zhàn)國、秦、漢時期,冶鐵業(yè)已普遍采用鼓風(fēng)冶鐵爐冶鑄生鐵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中記載的卓氏、孔氏等大商人,憑借冶鐵技術(shù)積累了巨額財富。
卓氏的祖先本是趙國人,當(dāng)秦攻破趙國時,卓氏被遷到了臨邛,在臨邛“即鐵山鼓鑄”,富到有僮(奴隸)一千人。卓氏利用當(dāng)?shù)氐蔫F礦資源,通過鼓風(fēng)冶鐵技術(shù),大規(guī)模生產(chǎn)鐵器,積累了巨額財富。孔氏的祖先原是魏國人,當(dāng)秦征伐魏國時,孔氏被遷到了宛,因在那里“大鼓鑄”,富到有幾千金的家產(chǎn)。
漢代歷史文獻(xiàn)中,提及冶鐵多稱“冶鑄”或“鼓鑄”。例如,《漢書·張湯傳》中提到趙國以冶鑄為業(yè)。《漢書·徐偃傳》記載徐偃矯制鼓鑄鹽鐵。漢武帝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年),西漢政府將鹽鐵業(yè)收歸官府經(jīng)營。次年,任用大商人東郭咸陽與孔僅管理鹽鐵業(yè)。東郭咸陽和孔僅奏請漢武帝在法律上規(guī)定:“敢私鑄鐵器、鬻鹽者欽左趾,沒入其器物。這一法律條文的制定,從側(cè)面反映出當(dāng)時鐵器主要由生鐵鑄造而成。
漢昭帝始元六年(公元前81年),西漢政府召集了天下的開明紳士所謂“賢良”和讀儒家書的所謂“文學(xué)六十多人來到京師,和御史大夫桑弘羊辯論鹽鐵和酒的官營政策。桑弘羊提到官府里有“卒徒作鑄鐵器”。他還提到過去豪強(qiáng)大家“采鐵石鼓鑄,煮海為鹽”。此外,桑弘羊還提到由官府“鑄農(nóng)具”,可使人專心本業(yè),不經(jīng)營未業(yè)。而賢良們則認(rèn)為官府“鼓鑄鐵器”,大都是大器,不適合民用)。從這些辯論中,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當(dāng)時鐵器主要用生鐵鑄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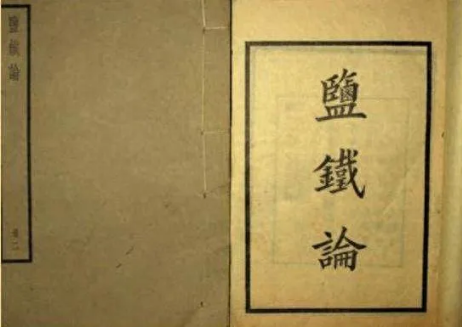
(鹽鐵論)
東漢時期,生鐵與熟鐵的名稱與應(yīng)用已見諸文獻(xiàn)。這些文獻(xiàn)記載不僅反映了當(dāng)時冶鐵技術(shù)的發(fā)展水平,還揭示了生鐵與熟鐵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應(yīng)用。
東漢時期,生鐵的名稱已經(jīng)明確。《淮南子·修務(wù)篇》中提到“苗山之鋌,羊頭之銷”,東漢許慎注解“銷”為生鐵。這也就意味著生鐵在東漢時期已經(jīng)廣泛應(yīng)用于鑄造和工具制作。生鐵不僅用于鑄造,還被用于藥用。《神農(nóng)本草經(jīng)》將生鐵列入藥用材料,記載其性寒及主治功效。
最古老的醫(yī)書《素問》中,也提及用生鐵落治療“陽厥”病”,這進(jìn)一步證明了生鐵在東漢時期的藥用價值。東漢時期,熟鐵的名稱也已明確。許慎在《說文解字》中解釋“鎩”為鐵之滅,即軟鐵,也就是熟鐵。
東漢時期,炒鋼技術(shù)的出現(xiàn)標(biāo)志著煉鋼技術(shù)進(jìn)入了一個新的階段。炒鋼技術(shù)是一種將生鐵加熱后進(jìn)行炒煉的工藝,通過將生鐵加熱至半熔融狀態(tài),溫度約為1200攝氏度。在半熔融狀態(tài)下,通過不斷攪拌,增加氧氣與鐵的接觸面積,使鐵中的碳氧化。隨著溫度升高,鐵中的碳含量逐漸降低。通過控制攪拌時間和溫度,可以將碳含量降低到所需的水平。脫碳后的鐵或鋼通過反復(fù)鍛打,去除雜質(zhì),提高材料的均勻性和強(qiáng)度。
1974年,在河南南陽東郊出土的一件鐵刀,其刃部是用高質(zhì)量的炒鋼鍛接而成。這把刀寬11.2厘米,長約17厘米,刀背厚約0.5厘米,形制較特殊。刀身有一道平行于刃部的鍛接痕跡,其刃部是用高質(zhì)量的炒鋼鍛接而成。
1974年,在山東蒼山縣漢墓中出土的一把環(huán)首鋼刀,刀身刻有隸書銘文:永初六年(公元112年)五月丙午造卅湅大刀,吉羊(祥)宜子孫。這把刀是用“卅煉”工藝制成的。經(jīng)鑒定,刀身含碳量在0.6%到0.7%之間,是用炒鋼鍛制而成。這種工藝不僅提高了刀的質(zhì)量,還使其具有較高的硬度和韌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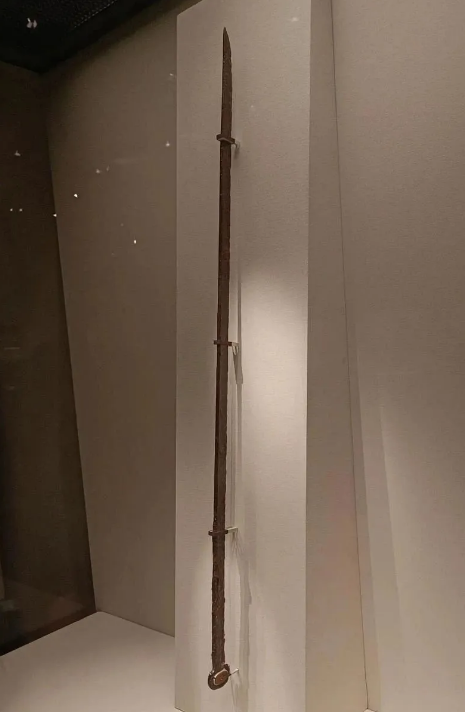
(漢環(huán)首鋼刀)
1978年,在江蘇徐州銅山縣駝龍山漢墓出土的一把鋼劍,劍把正面刻有銘文:建初二年(公元77年)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湅孫劍。經(jīng)金相分析,劍體是由珠光體和鐵素體組成,層次分明,各層的含碳量存在差異,最高為0.7%,最低為0.4%。這種工藝使得劍身各部位的含碳量根據(jù)實際需求而有所不同,因此劍身柔軟且劍刃鋒利,屬于高級階段的百煉鋼。
由于炒鋼技術(shù)的提高,東漢時代出現(xiàn)了“百煉鋼”。所謂“百煉鋼”,即將炒鋼反復(fù)鍛打,每加熱鍛打一次稱為一“煉”,通過多次加熱、折和鍛打,使鋼材的組織更加致密,碳含量更加均勻。每次鍛打后,鋼材中的雜質(zhì)被進(jìn)一步去除,最終形成高質(zhì)量的鋼,這種工藝不僅提高了鋼材的強(qiáng)度和韌性,還減少了鋼材中的夾雜物,使其更適合用于制作兵器。
東漢時期的百煉鋼技術(shù)不僅在中國廣泛應(yīng)用,還通過貿(mào)易和文化交流傳播到了周邊國家。1961年,在日本奈良縣天理市東大寺山的一座古墳中,出土了一把帶有“中平年號”的鋼刀,刀長103厘米。銘文顯示其為“中平口年五月丙午造作伎,百練清剛。上應(yīng)星宿,下辟不祥”。其中,“中平”是東漢靈帝的年號,時間為公元184年至189年。
 手機(jī)版|
手機(jī)版|

 二維碼|
二維碼|












